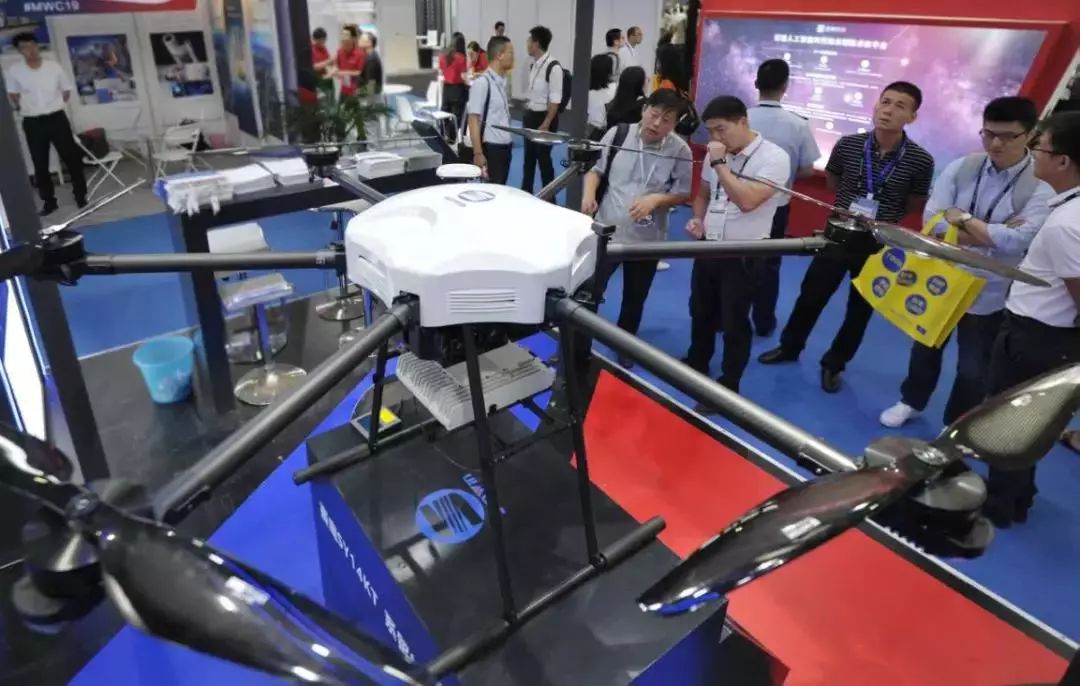我与文学丨谭岷江:我的爱好码字史

我的爱好码字史
谭岷江
许多年前,有个年长且与属相相同的师兄,他工作认真,却没有什么爱好,便一直害怕退休后不习惯于那种宝贵的时间自由。我劝他提前培养和学习几个爱好,为退休生活提前做好准备。我说,我爱好多,比如我退休后,除了打小麻将,我还可以有钱时去旅游去购物,没钱时码新字读旧书。我说的码字,其实就是闲余堆砌文字,说文雅一点,也算是高尚的写作,不过,因为从没写出名堂和挣到大钱,所以我最多只能算一名兼职码农。
俗话说,三岁看老。现今绝大多数爱好写作且爱得太过纯情坚定的人,都有一个喜欢文字的童年,就像我无比思念小时候只吃过两三次的面条小米粥和玉米粒焖洋芋老黄瓜饭一样,我似乎也不例外。我的爱好码字史,大概可以从17岁那年发表散文处女作正式开始,但要想追溯起源,却可以从更小的时候着笔。
7岁那年,我本该到大队小学入学一年级,可是因为家里太穷,父母最初便有意让我继续在家。我因为跟着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学过几天的字,对知识有些向往,便有些伤心,记忆力和模仿力还勉强的我,就将父亲当生长队会计时的一些空白账簿撕下来,自己胡乱编了两三页语文课本,第一课也是自编课本中唯一的一课,便是我尝试写的第一篇约五六十字的短作文。事后,父亲很气愤,想打我,又舍不得下重手,便用俗称“梨酱壳磕转”的手法,伸出弯起来的右手,用食指和中指狠狠地打了我的脑壳。小学里唯一的公办老师知道了这事,专程前来考了我,让我跳级去读他任教的二年级,并每学期均免除一元八角钱的学费,还可适当给一点奖金。再后来,因为看了大哥带回来的《三国演义》和《第二次握手》,便有些模仿码字的冲动。父亲每年又大方地拿出两角七分钱,给我订了一个季度的《中国少年报》;又给我买了《算得快》《常见成语故事》等书籍,我均读得津津有味。有一次,语文老师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字都有稿费,两分钱一个字,连标点符号都算钱。我便很激动,赶紧半模仿半原创地写了一篇关于油桐花的作文,找母亲索要一角钱,说是一个月后就能收到十几元钱。母亲很高兴,觉得这是笔天大的生意。我买了八分钱的邮票和一分钱的信封,将作文寄了出去。谁知左等右等,一直都没有消息,害得我每次遇到母亲,就觉得做错了什么,觉得自己是个小的大骗子。
此后进入初中,一直有阅读和码字的爱好,但再也不敢投稿。那时,我只是心痛那昂贵的邮资,并不知道有些报刊的投稿可以只花一分钱,在信封上写上“投稿”“邮资到付”即可。考进石柱师范后,开的课程再也没有初中辛苦,便爱上了图书室,也爱上了码字投稿。说起来,我一直对我的情商很自卑,但我在借书上的情商真的非常优秀,视野之内,似乎还没有我借不来的书。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师范,我都能与图书室的女管理员老师和有图书的同学、村里有书的长者建立友好关系。小学图书室的书籍并不多,我只从管理员老师那里借到了几本《金光大道》连环画,但我和班上有图书的男成同学、女张同学、女吴同学关系很好(成同学的父亲是脱产干部,张同学的父亲在外当裁缝,吴同学住乡场上,有亲戚是大官,乡间更是传言是万岁军吴军长,家里都比较有钱且乐于投资买书),借了不少书和连环画来读;初中图书室罗老师经常把没登记的新书第一步借给我(比如像现在《人民文学》开本的《射雕英雄传》),师范王老师更是放心地将图书室钥匙交给我,全校只允许我一个人进图书室。
因为当年读师范不交学费,还有国家补贴的生活费,且将来包分配,所以父母便给我的零花钱便多了一些,我便能随意买邮资来投稿了。但投了许多次,都没结果,退稿信倒是收到许多。不久,在小学任教的二哥支持我的文字梦,给了我15元钱,参加了广州散文诗报举办的函授班,记得班上同学现在最出名的便是当年云南某大学任教的成都名家邓贤(记得这个名字,除了他是大学老师,还在于《三国演义》中刘璋手下有个大将也是这个名字,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在能读到他的许多作品),结业后在散文诗报上发表了一组散文诗。但这只算作业作品,不算处女作,我真正发表的处女作是在叶圣陶先生逝世一周年那天,我在《天津日报》副刊散文专版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说起来也有些玄幻,因为我本来是投给《散文》杂志的,大概是当时的编辑贾宝泉老师觉得不适合杂志,但适合报纸,便将它推荐给了天津日报的宋曙光老师——可我一直不知道这其中的周折,所以语文老师看到样报信后,就先拿去学校教职工中宣传了一下,却派同学来通知我,我便觉得是骗局(此前曾被某位同学拿退稿信戏骗过一次),因为我从来没给《天津日报》投稿。最让我欣喜的是,仅仅三天后,稿费就寄来了,本来才1500多字的小散文,居然按1600字给了32元,果然是两分钱一个字——而当时学校有的老师每月工资才50元钱左右。
师范毕业后,我先在小学、初中和职高任教,后又转到行政部门,现在又回到学校。转转悠悠的期间,虽然我天生惰性,喜欢嬉戏与玩乐,且多数时间教学或行政工作都很繁忙,但一直都不敢被癞蛤蟆比下去,总在努力地零零散散地码着文字。实话实说,我纯文字写作的收入一般每年只在三五千元左右,最多时也不过七八千元,甚至不及是专业作家的我的文学院班同学的稿费退税收入。但好在码字真的有码字的乐趣,它至少让内向但不缺乏实诚的我结识了许多爱好文学的师友,让本来朋友圈很狭窄的我能够有幸和许多文友结交,有时喝醉了酒,或在电脑桌前坐久了走出屋来仰望天空,在神志恍惚间,真觉得自己就是社交面很广的基层成功人士。
17岁那年春天,《天津日报》的稿费单到后,我去县政府对面的老邮局取款,那时没有身份证,也忘了找学校盖章证明,但我一看汇兑员是我初中同学高帅哥的大嫂,便很高兴地作了自我介绍,我从父母嘴里听到的她公公家与我家是相识说起,又提到我父亲的名字和她公公的名字,再到万朝乡坡口乡是老乡,再到我和她家先生的弟弟是同学,说了大约三五分钟,大嫂终于相信了我,只让我展示了石柱师范校徽,便给我取了这笔当时算起来很丰富的巨款。
2019年8月,我独自到西安去旅游,喜欢历史的我很想到潼关去看看。但在旅行社问来问去,在网上查来查去,西安没有旅行社开设潼关旅游业务,我便决定自己坐火车前去。为了将潼关的历史文化景点都游完,我决定找一个当地的文学师友。但我对潼关确实不熟悉,掏出手机翻了翻西安的熟人,想来想去,只给2012年7月在四川阿坝州有过一面之缘的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张姐发了个短信,简略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这人就是这么内向,求人办事时总不敢亲自打电话,只是发短信,如果对方为难或者本就不乐意,则完全可以视作没有看到短信。——不过,大约晚上十点后,张姐发来消息,说她刚才在外面开会办事,回家后才看到我的短信,她已经通过同是省作协副主席的渭南市文联李主席把一切都联系好了,让我直接打潼关县文联李宏弟主席的电话。
第二天上午,我坐车到潼关。李主席请我吃了午饭,便开着借来的车带我去游四知堂、三国马超大战许褚遗址、风陵古渡、潼关老城和潼关博物馆。整个下午游得尽兴且时间紧凑,让我对潼关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个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码字这么多年,我觉得码字是我生活中最亮眼的一抹点缀,是展示我今生意义的唯一花园,更是我众多休闲方式中的一种方式。我自知天资庸质,且无坚韧的毅力恒心,码的都不是万里长城,只是小小的亭台墙栏,可谓半天打鱼六天半晒网,精神收获和物质收获都不值得一提——喜欢历史地理和文化、模仿力较强的我,更多的物质收获和精神收获在帮人代笔或撰写影视脚本、项目规划、文史书籍、新闻通讯等方面。——但我喜欢纯文学写作这码字的乐趣,尤其喜欢和众多文学师友一起神吹乱吹的感觉,也很陶醉于有些文学师友和领导对我的真情鼓励与深厚关爱。
为此,我依然爱着文字,爱着码字,爱着这很美好的人生。至少,退休后,再次实现时间自由的我在寂寞无聊时,不用去学着跳坝坝舞——我想,小城的坝坝比较小,电脑上的坝坝应该远比头顶的天空还辽阔,文字的舞蹈之美,肯定也不比所有有着美腰的中老年男女们跳得差。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